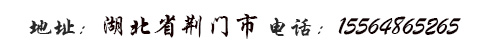延堂金石题跋选
|
浙江治疗白癜风医院 https://m-mip.39.net/nk/mipso_4342722.html 目次 延堂金石题跋选 00x0延堂金石題跋小言 01題金石佳好樓藏林乾良舊藏司母戊鼎銘拓本 02吳王余祭劍拓本跋 03唐開元十年月宮鏡拓本跋 (以上題金選三種) 04漢祀三公山碑拓本跋 05漢馮煥闕銘文拓本跋 06北魏溫泉頌拓本跋 (以上題刻石選三種) 07漢“海內皆臣”磚拓本跋 08漢“壽幣山陵弗寋弗崩”磚跋 (以上題文字磚選二種) 09陝西漢雙鳳仙草磚拓本跋 10漢泗水撈鼎畫像磚拓本 (以上題畫像磚選二種) 11燕下都雙龍背項饕餮紋半規瓦當拓本跋 (以上題瓦當選一種) 12《集王羲之書千字文》帖冊跋 (以上題帖選一種) 以上共計十二篇 00x0 延堂金石題跋小言 《莊子·天地》云:“金石有聲,不考不鳴。”斯以鐘磬之器而論萬物感應,借以論金石學亦恰如也。往古遺文存而不泯者,後人如不加珍重,則沉默不宣,雖多以骨彝碑磚之類,值於珠玉金貝之珍,問津無人,則啞然頹然,每令人喟歎傷感;且文物代有出土,亦代有毀滅,千百年無恙之遺存,如遭煮鶴焚琴之人、魚目混珠之手,更令人悲哀扼腕。是以吾人宜叩金石之聲,以延續其生,亦需學法精專,護古融今,方不愧乎先人而不罪於後世。故金石之學,雖非顯學,實在重要之學也。 金石除以實物面世,其打本尤宜傳遞觀賞、佐證研究;學者題跋,又常點綴升華,故亦為世人所重。然今人題跋,其弊有五:大字惡書,飛揚跋扈,毀其古雅氣息,其一也;逞強長言,喧賓奪主,傷其主次之宜,其二也;學力不逮,言不及義,失其治學之本,其三也;直錄經史,幾無主見,勤於抄書之習,其四也;炫目裝飾,追逐時尚,現其名利之心,其五也。此五端者,欺世無知,不可不以為戒。其俗或可醫,而其人恐不自以為病耳。是以題跋亦為學,並可觀題者識見懷抱,要之,不可以利與名系之,君子喻於義,方可與論品位焉。 治金石之學與題跋者,前人尚以考據。是以有考據之金石學,亦有考據之題跋也。考據之事當錙銖以校,不可等閒視之,每使古物得名,學術有功;然古跡孤群不一,史學價值不同,有不可考據者,有不必考據者,吾人勿以其不可與不必而輕視之,亦勿於不可與不必處強加因果。馬叔平先生云:以古人遺文貢獻史學者謂之金石學。史學者,國故學之基礎,而金石學,實在綜合之學,非有限於史學矣。金石者,亦不可僅視為史證之材料耳。是以別有義理之題跋也。竊以為義理之題跋最重,百般考據,若無關義理,則徒獲磚瓦,難為建築,徒有水土,難為建樹,故吾人撫古跡、觀佳拓,不可無興發感動之心、格物致知之思焉。若能依考據而悟義理,則達人亦當頷首。至於辭章,乃考據、義理所憑藉,此二者可無辭章之能,而辭章若無此二者,則空文耳;唯題以詩詞者,時或不然,而詩詞所題,雖可無跡以求,然亦須恰切其題也。蓋考據,米之炊而為飯,辭章,米之釀而為酒,至於義理,加飯之酒也。 余近歲頗慕金石之學,已遠見其門牆,亦常題跋,則無論拓本之名其盛與寂,拓本之形其巨與細,皆專注嚴肅為之,雖不足以自矜,然精誠所至,亦不至於自愧也。余嘗戲言雖無考據之能,然亦可謂義理派題跋者,若名余辭章派,余所不允也。題跋雖小,然其中義理感發,或可為同道知音之加飯酒乎? 庚子春月,檢數年前舊稿,略加刪定,獻曝於友好并求正焉。 延堂魏暑臨於沽上知夏書屋 1 題金石佳好樓藏林乾良 舊藏司母戊鼎銘拓本 滄州趙氏金石佳好樓庋藏拓本上品甚夥,去歲示以西泠林印迷先生舊存戊鼎拓本,罕覯珍玩,神采穆穆,可謂吉金極則在焉。惜銘文至簡,近歲“司”“后”之爭又熾,人言各殊,一時難斷。因受命跋尾,乃選讀論文若干,紛紜爭辯,常未卒讀而頭痛欲裂也。 余以為此二字之爭純乎文字學事,吾人賞藝玩味,一字之論斷,在可與不可之間,至若成段銘文,亟關乎史實者,則當別論。余本非輕信武斷之人,既讀近代諸家大著,更不敢有所定讞也。 《說文》云“司”“從‘后’反”,世人或依此而定為一字,而許氏之論,原以為兩字也。且其依據戰國至秦漢文字,實未見甲骨及西周金文。以後代之論繩準古人,是治學大忌,況吾人又後其後也。此余所引為戒者一也。 且漢距商周之遠姑置不論,即單言商、周,檢其文字,別體既繁,演變又劇,欲一言蔽之,何其難也。近人常欲概言定律,不知別例一出,“定律”破矣。或曰甲骨文“司”“后”絕然不分正反;或曰早期二字形皆為“司”,“后”為後起義;或言早期皆“后”,“司”為後起;或言先秦典籍“司”並無祭祀、后嗣之意等——此類定律之論,余皆不願輕採,因其所舉,皆論證已意之例也。且今人所見者,非古跡之全體,故以現存辭例為佐證可也,定論則不可也。以一概全,皆近推論,存之足為可貴,獨尊難副眾望矣。此余所引為戒者二也。 又此二字爭論,似與“辛”銘銅器出土相關。“司母辛”“司辛”銘文絕類此器,然容貌酷似者未必親兄弟,只宜旁證參考,不可簡單比附。又有引《尚書》《詩經》《爾雅》《白虎通》等書者,皆如聞鄰人隔墻耳食,非主家親傳口授也。諺云:遠親不如近鄰,近鄰不比本人,其語雖俚,然足為學者鑒。余非好疑古而輕旁證者,唯不願喧賓奪主耳。此余所引為戒者三也。 故余獨賞徐中舒先生《甲骨文字典》云:“司……象倒置指柶,柶所以取食,以倒柶覆於口上,會意為進食,自食為司,食人食亦稱司,故祭祀時獻食於神祗亦稱司,後起字為祠,氏族社會中食物為共同分配,主持食物分配者亦稱司。”取諸象形會意,合乎時代背景,立論簡明,直令人吐氣暢神。是故余不願多作糾纏,徑稱其“司母戊”可也。 早期銘文,不重辭彩,無非紀名、紀事二體。或云“司母”即“嗣母”,則與“后母”說內涵雖異,而句式相仿,皆紀名也。余雖未學,總覺此三字銘文若僅屬稱謂,似不及敘事之辭更適于禮器也。此直覺之論,更何待乎考證耶。釋卷再觀斯拓,卻如故友久違,仿佛耽讀論著之時,神交已為之誤矣。因題俚句云: 至簡雄奇戊鼎文。標名紀事總難分。誰從謎底追迷面,枉費群賢考據勤。 皓首窮經耽一字,神姿韻味恐難尋。直觀本自成真賞,足慰今人慕古心。 未必新風馳舊雨,應循故道探前村。勿愁相見不相識,且訪炊煙各自門。 柳暗花明景色真。山重水複認前塵。高鄰且莫通名字,已借形容辨主人。 歲在己亥春月 沽上延堂魏暑臨於知夏書屋南窗 2 吳王余祭劍拓本跋 此近歲餘杭南湖所出古劍,自曹錦炎先生考為吳王余祭劍,頗為世人所重。其銘至為精美,文曰:“工吳王{虘又}矣工吳擇其吉金,台(以)為元用。又(有)勇無勇,不可告人,=(人)其智(知)之。”董珊先生曾博引古籍,釋末三句之意為:有勇不宜言說,人能知其為空言,故宜示人以實踐,是為力行之勇德也。李家浩先生以為:“不可告人”之“人”指他人,“人其知之”之“人”指吳王自身,所述乃兵家韜晦之術,並參以《六韜》“大勇不勇”“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聖人將動,必有愚色”諸說。竊以為“有勇無勇”確偏義於“有勇”,“人其知之”之“人”則未必指向自身,所謂不以有勇告人者,蓋以人自可知我之有勇也。若如是,則既存韜晦之用意,又顯擅勇之自得,其為銘文,不亦宜乎。 歲在丁酉夏月 沽上延堂魏暑臨於沽上知夏書屋 3 唐開元十年月宮鏡拓本跋 此沽上雅頌齋張公音濤先生傳拓唐開元十年月宮鏡,為鏡銘文字最多者,其辭曰:“楊府呂氏者,其先出于呂公望,封于齊八百年,與周衰興,後為權臣田兒所篡,子孫流迸,家子(于)淮揚焉。君氣高志精,代罕知者,心如明鏡,因得其精焉。常云:秦王之鏡,照膽照心,此蓋有神,非良公所得。吾每見古鏡極佳者,古今所制,但恨不得停之多年,若停之一、二百年,亦可毛髮無隱矣。蘄州刾史杜元志,好奇賞鑒之士,吾今為之造此鏡,亦吾子之一生極思。開元十年五月五日鑄成,東平郡呂神賢之詞。” 上海博物館藏月宮葵花鏡,除外飾葵花邊緣,其餘絕似此鏡,唯月宮圖案實顯粗重呆板,了無神采;而其“明鏡”下為“曰”字,“東平”下為“邵”字,陳佩芬先生編著《上海博物館藏青銅鏡》一書以釋之,陳尚君先生輯校《全唐文補編》亦從之;今視此鏡,“曰”字處實為“因”字,且於文意更為暢達,“邵”字處實為“郡”字,且東平郡在山東,與呂氏郡望相合。 諦觀此鏡圖景,細致入微,刻畫生動,桂樹裁枝剪葉、精巧得宜,玉兔目光體態、靈妙有神,蟾蜍跳躍,猛虎食鹿,清晰可辨毫芒。陳佩芬注曰:“獸鈕,獸口中噬咬一馬”,較以此鏡,鹿之角、蹄俱甚分明,實非馬也。且其獸之形,應為虎也;余聞或有以屈原《天問》“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等古籍為證,持論古人以為月中有虎者,良有以也。 昌慶志先生著《唐代商業文明與文學》以為:呂、杜二人無私交、隸屬關系,銘文卻遠述先世,旁及秦王之鏡,乃商業宣傳行為。然余讀此鏡銘文,深感呂氏千載之心!其得鏡之神理者,無非今人所謂工匠精神之所在乎?而其能不止於巧制,其志有照乎心神。千載以下,張公嘉拓精華,鑒以謹嚴,顯其毛發,知者代有,良公亦得,其真可對視古人、會其極思者也! 因題《浣溪沙》一闋云:拂去千秋鏡上塵。照心照膽識前人。燈前校讀補唐文。幸有珍奇毛髮現,乃知工匠亦精神。融今證古在存真。 歲在丁酉春月 沽上延堂魏暑臨題於知夏書屋晴窗 4 漢祀三公山碑拓本跋 古人作書,有可法、不可法之別,自漢祀三公山碑現跡於世間,名家取法繆篆,成功不鮮。而此碑之書體是篆或隸,卻言人人殊。 楊守敬《平碑記》“非篆非隸”之說,流布甚廣。然非彼非此之論,畢竟不成語也。蓋近人觀之以形似,仿佛此碑兼有篆、隸兩體之風格,而言其非篆非隸,則不可也。 又如翁方綱《兩漢金石記》雖以之爲篆,卻又言“由篆入隸之漸”,康有爲《廣藝舟雙楫》以爲此碑書體爲繆篆,然亦持由篆而隸、篆多而隸少之論,且評爲“分書之宗”。竊以爲,就此碑之作書者而論,自不排除其或許存有雜糅篆、隸兩體之主觀意願,然以上諸家持論口吻,似非爲揣度其作意,而皆以書法史論出之,則恐皆以客觀之論調而失論斷之客觀者也。 今人桑椹《東漢〈祀三公山碑〉早期拓本流傳及其後世影響》一文曾詳加論述,以爲元初年間已屬東漢中葉,隸書流行,地位確定,已無由篆入隸之“過渡”可言,早期學者多囿於隸書概念藩籬,除因時代局限,尚無清晰書體演變分期之歷史觀念,更因過分拘泥圓勻婉通之篆書觀,以爲篆書必圓而方者必隸書矣。翁氏“減篆之縈折爲隸之徑直”之論正此類也。方折篆書實非罕覯,彼時學者多以爲古隸,亦緣乎此也。況且此碑之書者是否如梁啟超所謂有“以隸執作篆”之主觀意識或不經意之實踐,又尚待考量也。 蓋彼時隸書既興,以篆書碑,原因無他,爲級別高而示莊重也。日人真田但馬、宇野雪村所著《中國書法史》云:不用通行字體而用篆,以表重視,而篆書圓綫減少、直綫增多,或已成風氣,世人以爲由篆入隸,則不確也,宜視爲“漢人的篆書”。可謂簡明扼要之論。 然而“漢人篆書”之概念亦略顯含混——若云“漢人作篆書”,則篆書古法仍在,唯漢人書寫而已;若云“漢篆”,則漢代篆書宜別是一種篆。就其論調,所謂“圓減直增”云云,似應爲漢篆乃篆書之新法別體也。然則漢篆既已爲新法別體,其體勢明顯之變化,更緣於何故哉? 杜香文引裘錫圭評曰:書者主觀欲書篆,而受隸書影響太深,故筆法近隸,字形趨同,蓋此碑乃隸書時代之人所作不標准之篆書也。余以爲篆書筆法,未可一概而論也,隸書時代之人是否有純粹篆書之觀念,抑或彼時篆書本可以如此寫,亦未可盡知也。又杜氏自云:此碑實仿古而未成,而愈加新奇可愛之怪體也。余亦不知此之所謂“怪”,所存何在也。此等論斷皆以爲時代既已更新,書者復古不完,故書體特異也。 究其實也,後人復古,所復之古,因時所異,往往不同。就今人言,秦漢是古,唐宋亦是古,皆歸爲古,我若復古,以誰古爲古,以誰古非古?固當定以時代也。吾人怎知此碑書者所復之古竟不爲方折之篆書耶?何其所書必圓轉乃可言篆,而書爲方折之篆則謂其復古之不完耶? 又,華人德《中國書法史》以爲此碑之書不屬書體之過渡,而由書者對篆書之隔閡所致,故書者非因不諳篆書而束手無策,乃是大膽創造,故華氏視此碑爲書者對古文字掌握之不自覺與書法創作之自覺相結合之產物。此誠新奇之論也,然據余觀之,此碑實屬“運用古文字之自覺與書法實踐之不自覺相結合之產物”,何也? 蓋此碑之書者,隸書時代之人也,故意選用篆書,乃爲體現莊重,此復古之行爲,固可謂對古文字之自覺也,且其所復者,或本方折之篆也。恰如今人寫古詩,未必直搗《詩經》,而不妨爲“古風”也。而其所書之字,似略帶隸法,無論因其囿於彼時所處之風氣,或緣於書者自身書寫之習慣,蓋其筆端自然流露,非刻意追求所謂篆書之“純粹”,故可謂書法創作之不自覺也。此亦恰如今人誦讀古詩,縱依古韻,而一時一地之聲口,一人之音色,容不可免也,然不妨古詩仍爲古詩也。然此與復古之完與不完,非一事也,“純粹篆書”時代之人作“純粹之篆書”,個體之間,亦未必如出一轍也。 此碑書風獨立卓群,難以旁證,似一空依傍而獨創其新,然自古所謂書風創新者,實無空中樓閣、憑空捏造者,今日所見獨特之屬,只如失群孤雁,唯因歲月遞遷,滄海桑田,古跡磨滅,不可計數,今人所見可參者,億中百十,何其少也。 且篆、隸二體,經漫長之轉化、複雜之演變,今人視某字筆畫、構件之爲篆者,或已屬隸之先型,視爲隸者,或仍篆之遺緒,非合涇渭之喻也。此碑之書者於篆書書體之“隔閡”只在圓方,此不可謂隔閡,因篆書本有方折者;於隸書書體之形態妙合神貌,亦不足謂創造,因並非所有方折之書皆隸書,且彼時隸書已大興也。彼時篆書,蓋正可如此也;而此碑書者一人之書風,亦不可不如此也。是以余未見其怪,唯見其真實可愛者也。 歲次戊戌春月具稿 夏月初伏後二日錄於沽上知夏書屋晴窗 延堂魏暑臨題 5 漢馮煥闕銘文拓本跋 世人金石並稱,而石學實自有門庭。漢人石刻,表出群萃,雄風炳著,氣魄貫塞天地之間,最稱顯要。此馮煥闕銘文久為海內珍重,其字體爽邁開張,如《曹全》同儕而性情愈加豪逸,字形如漢簡牘書之率真,用筆似直以鐵錐刻劃石上,觀之若呼吸天山橫雲,心胸為之開朗。洪盤州以其為八分書,且符張懷瓘“騰氣揚波”之說,康南海評其為“隸書之草”,因其“布白疏,磔筆長”云云。啟元白《古代字體論稿》以為:漢魏之際,隸書出現筆劃輕便之新風格,省卻蠶頭燕尾,為後世真書雛形,為與此新隸書相區別,乃增舊隸書“八分”之名;八分者,八成古雅之體也。此銘極似手書,略已“輕便”,蠶頭不在,燕尾尚存,其所造作,蓋正與彼時“八分”概念興起之時相近,而較其所謂之“八分”體書更略呈新體,宜在新舊隸體之間也。至於康南海所謂隸書之草者,余以為隸書即彼時手寫之便體,恐反為隸書之正者也。 歲在丁酉夏月 沽上延堂魏暑臨獲觀並跋 6 北魏溫泉頌拓本跋 北魏松滋公元萇溫泉頌拓本,余丙申冬於友人處曾見一纸,惜其舊拓且殘,怜而購得之。斑駁天然,雖殘猶寶,因寄吳門徐松盦先生,倩良工裝池,止其零落,復其莊茂,可谓樂事者也。去岁幸復得此纸旧拓,既近完整,莊茂更显,亦实可谓良缘。 莊茂者,康南海《廣藝舟雙楫》以評此颂之書也,可謂善評者矣,然與《孫秋生》《長樂王》《太妃侯》諸刻石相較,此頌尤顯敦厚溫和。乾隆《臨潼縣誌》稱其“書法機圓體方,於羲、獻後別開形制,為唐歐、褚諸名手所自出。”是賞會之言,良有以也。 且其文辭可誦,銘志可感,蕩穢療苦,君子所泊。據聞乃溫泉之首見於金石文字者。張自修編著《麗山古跡名勝志》云:俗以麗山華清池得名之由来歸於左思《三都賦》“華清盪邪而難老”句,顯然不妥,李善明言彼“在廣平都易縣”,即今河北易縣溫泉,麗山池名實發端於此頌“淵華玉澈,心清萬仞”之句,至王褒《溫湯銘》則直言“飛流瑩心,華清駐老”,而唐玄宗遂命名曰華清宮。此是辨證之言,亦足記也。 曩得残本,松盦云:舊拓無人珍賞,則命運破敗如斯,唯吾輩得而寶之,題而跋之,則反復可觀,古今生輝。余特然其說,曾並識之。得此全本時,紙脆不忍展觀,所幸敷裱為時未晚,折處略有失落,亦無奈者也。此本舊有“趙汝烈字子勳號龍嵠石安布衣生平好結金石緣”印記,趙氏西安人,六十餘載前曾自訂《研世軒印譜》,其金石之緣,今能接續,不亦宜乎。 歲次戊戌夏月 沽上延堂魏暑臨於知夏書屋晴窗 7 漢“海內皆臣”磚拓本跋 漢“海內皆臣”磚文,有顯然為“飤”字者,從食、人,然世人多不識,更有絕似“飢”者,故世人多釋為“道毋飢人”。 或曰,此實在兩種磚也,字本不同。余以為其磚既出同一地域,且所用莊重,不宜有一字之差也。 或曰,十二字者字多似“飢”,十六字者字多為“飤”。然余亦曾見十二字而顯然“飤”字者也。 或曰,此磚“飢”字之“几”,上端多有一短尖筆,蓋“人”字之變形也,且“飤”字既明確不可易,則皆實乃“飤人”也。然則其義何解耶? 李零先生數年前釋為“食人”,即“人或獸吃人”之意(《“邦無飤人”與“道毋飤人”》),此不免今人臆斷之嫌,“飤”雖有“吃”意,然西漢人謂“食人曰飤”,即予人食也,陳直先生《讀金日劄》曾論之,是故“飤(食)人”非“吃人”,而實如段注《說文》所謂“以食食人”者也,或“以食食人之人”也,蓋豐年民足,不需接濟他人之意也。 且余另見一種磚,銘文為“漢廣皆強,歲登成熟,道毋‘飢’僵”,如釋為“飤僵”,何以符李氏“吃人”之說耶? 又,馬驥、任平曾作文釋為“需要喂食之人”,即乞丐(《山西洪峒縣新出的漢十六字吉語磚》),李氏以為亦好,只嫌於古書無舊例。然據余觀之,似更與古人詞法不合也。 歲次丁酉秋月 沽上延堂魏暑臨於知夏書屋 8 漢“壽幣山陵弗寋弗崩”磚跋 漢“壽幣山陵弗寋弗崩”吉語磚。 “幣”同“敝”,前人有訓為“終”“盡”者,復旦大學沈培教授更於十年前作《“壽敝金石”和“壽敝天地”》長文,博參古籍,釋其義為“壽與山陵相終”,而山陵弗寋弗崩,既無所終,故人壽亦永。其說甚恰切也。是以古語雖短,模棱兩可之解亦或可通,終不如考據穩妥,以逆古人之志也。然則此磚吉語,曲折玩味之致現也。 “寋”同“騫”,《詩經·小雅·天保》云:“如日之恒,如月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何以古人每比壽以山耶?夫金石不可損耶?或曰:此吉語也,未可深解也。然曾文正公《冰鑒》云:“山騫不崩,唯石為鎮。骨之謂也。”是以羨山之骨堅,而生永葆之想也。今人觀之,不宜發懷古固本之思乎。 丁酉春月 沽上延堂魏暑臨於知夏書屋 9 陝西漢雙鳳仙草磚拓本跋 余嘗戲言曰:鳳若實有,必為猛禽,否則無以為鳥王。客曰:鳳修文德以朝百鳥,君何比之於鷹隼耶?余曰:是猛者,非暴也,健勇之謂也、生動之謂也。古人之美鳳,可稱極也,然六像九苞之說,嘉祥來儀之景,誰得見耶?誰真信耶?權以為想往寄托可也。而世事凡極端虛構其美者,文化愈明,其信愈減,每嫌空有其名,空效其儀,而無生氣也。觀百年前晚清運數,不可知耶?君觀此陝西出漢畫像磚,雙鳳伏身,對向仙草,銳喙捷軀,翎毛疏朗,與君日常所見絢麗其表而呆若木雞者有類乎?此種生猛活躍,莫非吾民初始之體魄乎?其與文德有悖乎?客曰:妙哉論也!此畫中靈枝絕似鳳之錦毛,何故也?余曰:此正與鷹隼之別也。客大笑,勸余題跋以記之。 丁酉春月 沽上延堂魏暑臨漫筆 10 漢泗水撈鼎畫像磚拓本 此南陽董傑甫先生傳拓漢泗水撈鼎畫像磚,車馬、鼓舞之形已至鮮活,岸上牽索、舟中窺尋之態亦為明晰,唯繩索尚顯垂軟,非盡勠力拉動之狀,蓋其描繪者,鼎影乍現之時也,故龍身未現,而未及齧斷其索也。 泗水撈鼎傳說漢代方有,故《水經注·泗水》有“鼎伏”之說,“亦云系而行之,未出,龍齒齧斷其系”,雖以為“孟浪之傳”而記之;《史記·秦始皇本紀》雖未言“龍齧斷其系”之說,然亦記始皇“欲出”而“弗得”之事,則暴秦之未應續有天下,可見也。 吾人讀古書,須知傳說未必非史,而記史不妨傳說,不可以事事真實不虛而責備之,而應讀得作者選材之背景、選裁之角度也,要之,在史學之態度也,而史學之真實,非止實錄之真實,而歷史規律與精神之真實也,故史書常不可不透過一層讀。何況其說縱是虛妄,然其為說,本已屬事實也,作者選用,其自未必信以為真,唯傳達歷史相對之真實及作者之態度也,此亦史學之態度也。《史記》皇皇巨著,所記傳說甚多,太史公獨不知其非實有者耶? 讀《始皇本紀》,知始皇行事,多與無稽之談相系,如求仙、伐樹、擊胡、匿形等事,因孟浪之說,施暴刑厲法,至於坑諸生、燔刻石等事,則世人更欲借無稽孟浪之端而叛逆之,而暴君之暴,庶幾近乎物極必反之勢也。以此視之,撈鼎之說,亦何孟浪之有哉。 戊戌春月沽上延堂魏暑臨於沽上 時頸椎正痛,勉力跋尾 11 燕下都雙龍背項饕餮紋半規瓦當拓本跋 己亥夏初,師友同與石門永昌博物館金石之會,于軍兄持此燕下都雙龍背項饕餮紋半瓦當拓本囑津門三友同題,倉促落筆不及,遂攜歸承命。時余正讀吳磬軍先生所著《燕下都瓦當文化考論》,闡述詳審,令後學無可置詞。然余觀燕下都瓦當作雙龍背項之圖者甚多,因思其形用意何在。一則,龍身蟠曲至瓦面上端,其勢似自然低垂相背,如角力相抵,察雙龍圖形瓦當,亦多作觸首抵角之形,與此類推,皆示力者也。二則,吳公論云,燕下都瓦當饕餮紋,雙眉已被省略,雙角則演變為格式化之“如意頭”形狀,而余察諸雙龍背項之形,宛如饕餮之攢眉,不知先民是否恰以此龍首相背之形,象彼饕餮獰厲之眉,而增神獸肅穆剛正之美乎。拙論既不免方家之哂,何妨更發揮俚句云: 皇天無極枉欣悲,世上風雲簷下窺。 警示人心知未盡,千秋神獸一攢眉。 歲次己亥端午之日 沽上延堂魏暑臨於知夏書屋酒後漫筆 12 《集王羲之書千字文》帖冊跋 此《集王羲之書千字文》拓本冊頁。檢其全篇,千文俱完,唯第一開“成歲”二字倒置,第六開“疲”字多一筆,第十開“誡”字少一筆,而無礙其整冊之蔚然大觀也。 世傳集王書千文多種,亦有今人製作,然風格浮躁者多,得王書真髓者少。蓋集字之事,非止於拼湊,其字之大小,行氣疏密,比例至於巨細,搭配關乎諧調,是以懷仁度廿載乃成《聖教》;今人巧極技術,集字而失文采,以其急於事功而無靜氣,匱於審美而少琢磨也。 另有顛倒《蘭亭》以矜能者,連綴新篇固無不可,而集字配伍不協,故知選用既宜定原守真,亦實見效於字之別擇與改良也。 所謂別擇,審周遭而揀選也,如同為“之”字,舒促不同,俯仰各異,選字則應參以所處位置,若為一行之首尾,則作用宜兼起興收束也; 所謂改良,為順暢以修訂也,放大縮小,協商角度,使其不廢於扞格,若某字跡獨存一種或杳然無存而循例施之通假者,則更賴乎此也。 余特重此冊,正因其完善有度,靜穆不俗,雖字出多本,而一體風度含蓄敦厚之故也。 古人集王書,《聖教》得靜秀雍容,《興福寺》得生動華美,而此冊大類《聖教》,其出於《聖教》之字亦實多,有模形重影者,有略加變化者,結字取筆、牽絲映帶,下原跡一等矣;且多幾分凝重渾融,品味又略通於定武《蘭亭》,起八大山人觀之,亦當頷首也。 右軍傳世法書之可信者屈指能數,匯成千文,良不易也,故亦有拼湊部首所成者,而妙於化工,非神交山陰者孰能為之哉?又有如第一開“劍號”二字,据余目及右軍遺存,似無此二字鴻跡,余是以疑集字者曾參考智永千文——此余或有疏忽處,如不然,則更可證集字者之體悟王書為深切也,永書實王書之繼也。 卷首刻有“閩侯官林恂季忱氏集晉右軍將軍王羲之書”十八字,余檢索史、集,唯明人宋懋晉《摹諸家樹譜》卷上,乾隆、嘉慶、宣統諸印後,鈐有“季忱”、“林恂之印”、“臣恂”等印,其餘竟資訊莫尋,是以數日寢食不安。何以百年人帖俱寂?蓋正因此冊集字雅正而不怪譎,使人有司空見慣之感而不之重也。且諦察其品,當為木版,水火之患,與石相較,本已倍矣。 聖者,古人賢能之特稱也,右軍以書得其名,千百年此一人耳。習王書者,能得佳範,幸更何如。余幸得見此本而臨之,更幸此本得存積善之家而不泯也! 丙申歲杪 沽上延堂魏暑臨拜稿 题跋者简介 魏暑臨,字子夏,號延堂,天津人,雅愛詩文書法,偶涉金石,現為中國語文現代化學會常務理事、中國語文現代化學會語文教育專業委員會副秘書長、中國成語文化研究會理事、中華詩詞學會會員、天津市詩詞學會理事等。著有《書壇巨匠吳玉如》等,各類作品散見於《中國金石》《集古傳薪》《九河尋真》《百年西泠·湖山流韻》《印學研究》《藝術中國》《書法報》《天津文史》《天津日報》《中華活頁文選》等書刊。 徐亞輝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ongchia.com/lcyl/6983.html
- 上一篇文章: 失眠症的原因与辟谷康复原理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